前情提要:七绝出世,楚缘远走,枢城的一番遭遇,毁了牙行,死了太守。倒也是见了居心叵测,前仇孽缘。平宣侯千里追拿魔婴,猪猴怪盗逃返霹雳堂,常思远继承太守位,常清莲遁水无形,金探手盘踞枢纽城,神秘的崔氏一家不知所踪。楚缘收拾行李,继续踏上永澜洲的路程,车马旅途近一月,腹中残剑安稳如故,但这王侯地境,往往不太平……
永澜洲位处惠王治地边境,地理偏南,山灵水秀,温度宜人,若逢盛夏,也是皇亲国戚钟爱的避暑之地。
而洲内百姓也是安居乐业,民康物丰,得益于惠王的治理,惠王李鼎,跟随开国皇帝传下来的异姓王之一,年过而立, 膝下暂且仅有一子,名曰李问鹿,深受王爷宠爱,几乎百依百顺。
惠王府中,众下人不敢抬头,齐齐跪在庭中,一盏琉璃酒杯“啪”的一声摔在地上,四分五裂。
“李大头,看你干的好事!把孩子逼得跑了出去,这下可好了!你还我孩子!我跟你拼了!”一位雍容华贵的少妇梨花带雨,精致的脸庞已经是梨花带雨,扔完酒杯后便举起拳头往男人身上砸去。
软绵绵的拳头毫无力气,男人还是装模作样的吃痛,哀求道:“爱妃,爱妃,莫要心急。”
“我怎么不心急,你这个没良心的,成天把孩子关府里,不然他能跑出去吗,现在丢了音讯,若是有个三长两短,我……我也不活了!”说罢王妃就往柱上冲去。
下人们吓得赶紧团团围住,被王妃叫做李大头的惠王李鼎,忙忙抱住爱妃,说道:“若是贼人捉了,给他们钱财便是,若是政敌拿了,他们更不敢妄动,惠王的儿子,谁来都得掂量掂量。”
“呜呜呜……”王妃依旧泣不成声:“我不管,我就要见到王儿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“那是当然那是当然。”惠王拍肩安抚道:“你们都给我听着,立刻安排所有人手,全疯情书库力追查小王爷下落,重点搜寻永澜洲,活要见人,死要……”
“呜哇!……”王妃哭的更大声了。
“额嗯……总之,必须把小王爷活着带回来!明白吗!”
“得令!”众人齐齐答应道,立刻下去部署去了。
“别怕爱妃,王儿不会有事的……”惠王紧紧抱住王妃,低声安慰着。
……
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枝缝洒在脸上,别样的暖意让鼻子有些痒痒的,小王爷低低哼鸣了一声,浅浅睁开睡眼,迷茫的视线渐渐才汇聚,只见面前的火堆余烬还冒着缕缕青烟,越过视线,洞外绿草茵茵。
“嘶……”小王爷挣扎着起身,却觉得周身酸痛,伸手一捏,却发现自己睡在一地棉衣之上,衣褥覆盖下的身体一丝不挂。
坐起身来一瞧,自己正躺在一处石洞之内,火堆旁还挂着自己破烂的锦衣,云靴,和……一双靴口浅清,周身洁白的女式布靴。
小王爷缓缓回头,只见身后的巨石台上,铺着一层薄薄的白布,白布上一具曼妙的背影,女人蜷缩背身,却能看到青白的衣裙下,盈盈可握的腰肢,和形状浑圆的玉臀形状,顺着臀股往下,收起来的双腿被身体遮住,但一双白净的肉色,却吸引了小王爷的目光。
只见眼前叠着一对小巧玉足,肌肤白里透红,伸近脑袋一看,表面光滑无暇,十根玲珑葱趾上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宝石一般整齐排列,看得人爱不释手。
小足如浑然天成,雪白柔嫩,精致玲珑,未曾妆点的指甲上却像天生染着豆蔻一般,粉嫩白皙,脚背上若隐若现的青色血管胜似白象牙上点缀的翡翠,光滑的足底起伏凹陷,曲线优美,肌肤纹理若不贴近细看倒难以发现。
而最迷乱小王爷神志的,却是足间隐隐散发出的淡淡清香,似是茉莉,又像是山茶,忍不住张开鼻腔,重重深嗅一口,只觉得清明醒脑,芬芳宜人,缓缓吐出了一口热气,悉数吹拂在光滑的脚底。
似是作痒,玉足轻轻收缩,白皙的足间轻轻摩擦,发出悦耳的莎莎声响,伴随着一声轻哼,小王爷受惊似的往后倒退,却拉扯到伤处,疼的哀嚎了一声。
“嗯?”楚缘听到声响,忙的睁开眼睛,撑起身子一瞧,那小孩子在火堆旁捂着肩膀叫疼。
“你没事吧。”楚缘翻下石台,玉足轻轻落在垫底的衣褥上,半蹲着扶住小王爷。
楚缘将小王爷转向自己,右手浅浅发力,一股温热的感觉传达到小王爷肩膀上,然后轻轻揉捏,泛紫的肩膀顿时松弛了许多。
而小王爷却只是呆呆盯着楚缘的脸,倒是忘记了疼痛似的。
“真漂亮……”
“啊?”楚缘疑惑的问道:“你说什么?”
“啊唔……没,没什么……”小王爷心垂下脑袋,试图避开目光,落在眼中的,却是一只伫在衣上的美足。
楚缘轻笑,一遍为眼前的小孩舒筋活血,一遍问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啊。”
小王爷移开目光,却又慢慢回到玉足上,轻轻说道:“李问鹿。”
“问路?”楚缘想了想,“哦,野鹿的鹿是吧。”
李问鹿点了点头。
“你怎么掉河里去了,深更半夜不怎么在家里。”楚缘问道。
李问鹿轻轻捏紧了拳头,不发一言。
楚缘瞧见,也不在多问,只是说道:“你的家在哪里,我先把你送回去吧。”
李问鹿说道:“过了永澜洲,往东走的惠城里。”
“惠城!”楚缘惊讶道:“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地方来了。”
李问鹿低着头,声音有些抽泣的说道:“我嫌父……嫌爹爹管的太严,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玩了……”
“你呀……”楚缘点了点李问鹿的脑门:“这不是让父母担心吗?”
瞧了瞧外面天色,楚缘说道:“既然天亮了,我们就赶紧出发吧,这里到下个镇子还有距离呢。”说罢站起身来,从石台上拿下一团衣物:“你的衣服不能穿了,暂且先用这些将就一下吧。”
李问鹿接过衣物,楚缘这才来到火堆旁,捡起烘干的布靴,拿下挂着的罗袜,坐在石头上,抬起一只小脚,双手捋好袜口,足尖轻挑进罗袜中,白皙的足面渐渐落入整洁的青罗小袜之中,待双足整理好后,才穿上还留着暖意的布靴。
“发什么呆啊,快穿好衣服。”楚缘提醒呆呆望着自己的秀气小孩,先一步出了山洞。
待到楚缘消失不见,李问鹿这才瞧见自己的身子,上身青一块紫一块,撩开衣褥看自己的下半身,顿时脸色通红,光溜溜的下半身,一根白净小肉杵直直伫立,白嫩的前端微微撑开小口,露出藏在深处的,被包裹住的一点嫩红。
在外面伸了个懒腰,楚缘舒服的长吸一口气,洞外吃着野草的马儿轻轻哼鸣。
“这地方真够远的,已经走了有半个月了吧。”楚缘抬手遮住阳光,只见山谷中树木丛生,百草丰茂,不时有林鸟飞落,只见远处的大河上,倏得驶过几艘快船。
“唉,我也想坐船啊,这山路太难走了。”楚缘叹道,一旁的马儿鼻间哼鸣。
“不是说你不好啦。”楚缘回头轻笑,却见山洞里走出一位灵气的小女娃,忙走上前去俯身笑道:“嗨呀,哪里来的小美女啊?”
李问鹿憋红了脸,提起袖子叫道:“这这……我怎么能穿女人的衣服!”
只见李问鹿身上套着一身绫罗绸衣,只是身形矮小,不得不多裹了一圈,长长的衣摆也扎进腰带里,手肘上一圈又一圈的褶皱,才露出两只小手。
楚缘揉了揉小王爷脑袋,笑道:“你就将就一下嘛,我这也没小孩子穿的啊,等到了镇上给你换一身吧。”
说罢回到洞中,将火堆熄了,收拾好衣服行囊,放在马后。
将马儿牵到山道上,楚缘登上马匹,伸手到李问鹿面前:“上来。”
李问鹿伸出手臂,楚缘将他一把提起,放在身前。
“父王都不曾再这么带我骑马了。”李问鹿心想。
“坐稳了。”楚缘轻驾一声,马儿扬起蹄子,稳当的朝山路前进。
楚缘握好缰绳,怀中的小王爷却心神不宁,只觉的脑后枕着软云,后背被柔腻环抱,面色微红,摇晃的马背上,前倾不是,后靠也不是。不自禁间,又觉得胯下咯腾,属实不好受,但又有点很享受。
未免太尴尬,李问鹿问道:“还不知道怎么称呼姐姐?”
楚缘悠哉的骑着马,说道:“我叫楚缘,从南云门来的,叫我楚姐姐就可以了。”
“南云门……”李问鹿沉思了好一会,似是没听说过,转而问道:“那你是侠客喽。”
“呵呵,”楚缘揉了揉李问鹿脑门:“我不过是个赶路人罢了,哪算的什么侠客。”
“那你给我讲讲你都去了哪呗……”
……
高墙深院,肃穆杀静,庄严的石狮子威武的伫立在漆红的大门口,两位身着甲胄的持矛士兵把守在外。
大门内,金器铛铛声回荡,透过门缝,只见火花四散,一团妖异的红色如缭乱的烟雾,是翩然飞舞的衣裙,带着艳火色的流光,突的亮出一剑,击在面前的铜人身上。
铜人轰然到底,胸口上青烟袅袅,竟是融开了一道小口。
红衣收招停歇,那如瀑的波浪红发下,洁白的额上一点红印,仔细一瞧是团真火朱砂。
“起来吧,奴家才用了多大点力气,少装模作样了。”
地上的铜人突然扭动,只听铜皮脑袋里轻叹声不止,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:“花大人,您这剑法越来越成熟了,这怕再过些时日,这铜甲也挡不住了啊。”
花焰瑾轻哼一声,袖口一挑,白皙的手臂翻开,只见一条黑蛇似的黑线从手肘显现:“有了下半卷剑法的支撑,这脉象总算是停住侵蚀了,只怕想完全根除,还是得将下卷学成才是。”
铜人艰难的迈步,走到花焰瑾面前说道:“万一那老头藏招怎么办,故意拖延您治病的时间。”
“哼。”花焰瑾双手环臂,胸前两团半裹的玉团被高高托起,呼之欲出:“他敢下绊子,那女孩就只有脑袋能见到他了。”
“啪。啪。啪”不远处传来三声掌声。
花焰瑾转头一看,只见从院外缓缓走来一人,肩绣金纹,身着白衣,发后一圈箍起,手中一折纸扇,气宇轩昂,见着如沐春风。
“好剑法。出招如快鸟穿林,剑锋凛冽淬火,令本侯眼前一亮啊。”宋流风身后跟着两个下人,走进院中说道。
花焰瑾理了理衣袖,一拉火红的长裙说道:“平宣侯驾到,奴家倒是有失远迎了。”
宋流风双手把着纸扇,笑道:“突然拜访,应是本侯该说对不住才是。”
花焰瑾嘴角一勾,揶揄道:“侯爷说的哪里话,奴家可担当不起。”
宋流风摇头浅笑:“只不过这剑法瞧着有些熟悉,也不知花大人从何处习来。”
“熟悉不熟悉,侯爷试试不就知道了。”说罢,花焰瑾下身一动,长裙里踢出一条白玉似的劲腿。
“啪。”纤细的脚踝被宋流风握在手中,只见花焰瑾裸着小足,柔糯的干净足底直直面向侯爷。
“是要与本侯切磋的意思吗?”宋流风笑道。
花焰瑾深深一笑:“还请侯爷为奴家指正。”
宋流风朝部下使了个眼神,二人抱拳喏道,便去院外把守。
“诶诶,二位兄弟,麻烦也带我一程,我这身装备不好移动啊。”
一边的铜人急忙喊道,惹得花焰瑾白眼微翻:“也不嫌丢人。”
二人气喘吁吁地扛着铜人的沉重肩膀,好一阵费力才搬出门外,刚一出门,里面便砰砰传来打斗声。
那铜人敲了敲铜头,吱呀打开一扇铜片,露出一个满头大汗的脑袋。
“唉哟不行,闷死我了。”铜人大口喘着气,将清新的空气吸入口中。
“好家伙,这一剑只是剑气快把这铜皮给烧穿了。”宋侯爷的部下看着铜皮上的一块剑痕,啧啧称奇。
那人憨憨大笑:“你别说,那老头的剑招是有些厉害之处,连我都收益几份呢。”
部下奇道:“什么老头,哪里请回来的高手。”
“唉,是咱大人抓回来的。”
部下勾起了兴趣,忙说道:“常言道入了花手,进了死门,头一次听说花大人抓了个活的回来啊,好兄弟,给咱哥几个说道说道?”
铜人面作为难,二人相视一笑:“都说南斜街的酒酿千里飘香,今日得闲,便请兄弟小酌一杯,可不要推辞啊。”
铜人一听便口舌干燥,在这铜甲里本就闷热失水,顿时勾起了酒虫,嚷嚷道:“那兄弟我却之不恭了,走着。”说罢迈着沉沉铜腿。
二人笑道:“先把你的铜甲卸下吧。”
还未至深夜,南斜街的酒巷也是座无虚席,此处毗邻京城里最大的一条烟花巷,名曰曲园街,一些风流之士偏爱风庸附雅,所以这条酒巷便更受粗俗的男人们的喜爱,喝到深处,到曲园街再开一坛,也不失乐趣。
三人来到装饰相对精良的宋娘酒肆里,好不容易在三楼找了个靠窗的作为,小二麻利的先带上了三坛酒,各自满上,那铜人早已渴得不行,径直端起一碗,咕噜咕噜仰头饮下。
“哈!好酒好酒!”
二人笑道:“兄弟莫要心急。”慢慢给铜人满上,“还不知兄弟名讳。”
铜人街过酒碗又是一口干了,咂吧着嘴说道:“鄙人姓张,张逆复,给花大人练剑的。”
二人相视一眼,奇道:“原来张兄不是朝中人士啊。”
张逆复道这酒,笑道:“不是不是,算是花大人看上我这练块的身子,带我进来当个练剑的罢了。”
“呵呵,能穿上那么沉重的铜甲行动,张兄也不是一般人呢,我二人敬你一杯。”说罢二人举起酒碗,张逆复拿起酒碗一碰,三人一饮而尽。
“张兄,我二人是平宣侯部下,就做些行宫差事,他叫猫儿狸,我叫狸儿猫。”
张逆复脸色微微泛红,打了个小嗝说道:“毛二里,李二茂。你们名字还挺奇怪。”
猫儿狸笑道:“侯爷手下太多,便给我们取了些好记的名字,我们索性也都这么叫了。”
狸儿猫搀着酒坛,喊道:“老板娘,上点下酒菜。”
“来啦!”
不一会,一位风姿绰约的裹着头巾的少妇端着一盆牛肉,一碗香豆,扭着小臀上了楼。
“尝尝店里的招牌牛肉,那叫一个下酒。”宋娘一盘盘摆下菜肴,却让张逆复目不转睛,
嘿嘿浅笑。
宋娘虽年过三十,却风采依旧,一副妇人打扮,但眼媚身腻,尤其是抹胸上忽的显出的两团白腻,晃悠悠的比之酒面的波纹。
张逆复嬉笑着红脸,悄悄伸手在宋娘胸前抹了一把。
“啪!”
“哟!”张逆复笑着收回手背泛红的手掌,还是盯着乳沟不放。
宋娘皱着鼻子笑骂道:“没看过,没摸过啊。”提了提抹胸,翘着指头指着窗外的楼阁说道:“那里的姑娘可水灵的多了。”
说罢招呼三人慢吃,又扭着丰臀走了。
“嗨哟这老板娘真对我胃口。”张逆复夹起一块牛肉笑道。
猫儿狸和狸儿猫又对视了一眼,说道:“张兄若有兴致,咱们之后到隔壁喝个第二轮就好。”
“嗯!”张逆复点了点猫儿狸,嚼着牛肉猛点头。
狸儿猫满上酒碗,说道:“咱先聊聊那教花大人剑招的老头呗,看这架势,咱侯爷多半也得费点力气。”
张逆复灌了一口美酒,哈道:“那可不,花大人把剑招融会了自己的内功,这才驶出那一剑炎刺哩,侯爷不明其理,这轮切磋怕是要吃大苦头……嗝。”
……
“哦……噢~嗯……啊哈~嗯……”
“啪……啪……啪啪……”
深院内,两道莫名的声响交织在一起,一滴晶莹的水滴从花瓣上悬悬欲坠,突然一只美脚落下,沉沉压下花枝,水滴飞溅,混入到一股散发着热气的浆汁之中,落在地上撒的杂乱无章。
“此次切磋……嗯……看样子还是本侯胜了呢。”
宋流风浅咬牙关,慢慢从嘴里吐出话来。
“嗯……哼……瞧你那……啊,瞧你那憋足劲的模样……啊……,怕不是再多磨一会,就得一泻千里……嗯啊!”花焰瑾躺在石桌上,火红的长裙当中散开,在桌上铺了个严严实实,娇媚的胴体风流曼妙,却成了宋侯爷桌上的称手玩物。
只见花焰瑾丰乳细腰,肌肤白净无暇,纤细的脖颈上头悬桌边,火红的长发想瀑布般挂在脑后,一团火纹在紧紧皱起的眉心微微变形,挺翘的鼻子上细汗浅出,火红的双唇被皓白的贝齿紧紧咬住,似是承受什么剧烈的感觉。
双手摊在两侧,手指紧紧抓握,火红的指甲却不曾伤到手掌分毫,那乳肉娇嫩挺拔,宋侯爷瞧的自在,只见乳峰巍然挺立,规模虽不似那枢城的美妇,但胜在乳峰红润,像是被朱砂染色,隐隐可见的淡绿血管从南峰蜿蜒落下不见,平坦的柔肚被双手握住。
花焰瑾蜂腰挺立,仅以后脊着力,只因侯爷高挑而石桌矮小,被侯爷双手托起,蜂腰下的柔腻丰满,才得以与侯爷的结实腰腹紧紧相拥。
“莫要小瞧了本侯,无论多少次,本侯……嗯……依然能让你丢盔弃甲。”宋流风听完花焰瑾的话,不怒反喜,激起了好胜的欲望,微微分开双腿,托着盈盈一握的柔软腰肢,将小腹猛地撞击在腹股之中。
花焰瑾娇哼一声,素腿反射般夹住男人熊腰,玉葱般的脚趾紧紧扣住,焰红色的指甲整齐排列,好似一个个红玛瑙。
“别……突然这么用力……嗯哈!”
花焰瑾双手捉上男人手臂,只怕自己给顶下桌去。抬起头往身下一看,越过摇晃不止的双乳,沟壑间,瞧见男子棱块分明的腰腹肌肉,腹下一杆雄壮的深入浅出的长枪直直捣进自己花道,搅的美肉颤抖连连。
宋流风埋头勇干,枪下媚肉蠕腻,交合处水光粼粼,而花焰瑾稀疏的阴户毛发,也是同火红的秀发一般,被淫汁打湿,杂乱的黏在丘上。
“噢哦~你怎么还不……嗯……,速速结束……奴家也要,也要遭不住了……”花焰瑾轻轻哼鸣着,手指关节捏的发青,只觉腹内一杆炙热坚硬的枪杆,在将曲折的花道褶皱一一剐蹭,宫口突噜噜的溢着浆汁。这根肉枪,温度比之火焰,让红袍火鬼也有些吃不消。
更要命的,那硕大有圆润的枪头,不时就挑上花径深处的一圈柔软,宋侯爷似是捉弄,将肉枪头向下一扭,倏得将那圈柔软挑了上去,整个肉枪牢牢顶在那藏而不见的玉穹窿之中。
“噢~”花焰瑾眉目圆睁,像是挑到了心儿一般,爽利不止,眼眸微微上翻,香舌吐露,一阵禁脔,那花口突自微张,像是打翻了糖心一般,飚出一注滚烫的浓厚蜜汁,温度竟然比宋流风的肉枪还要烫上几分,好似岩浆泼在枪上,密不透风的花穴内,尽也冒起一丝丝灼热的气雾。
“唔啊!”宋流风吃烫,寒玉红缨枪在穴内抖动不止,瞬间一股麻意直冲脑门。
宋流风深知此乃花焰瑾死穴,某一次媾和偶然从她口中得知,花焰瑾宫口下方有一处隐秘之地,腔肉肥厚,被紧致的宫口紧紧遮掩,若是一般人,定是尝不到此种滋味。
只是宋侯爷身怀利器,只在里面稍许捉摸,便找到法门,用粗长的枪头将宫口挑开,那下方黏腻幽邃的密室便暴露无遗,一般女人的此处换做“玉穹窿”,别就是最为细嫩紧致之处,只是大多人的耕耘,难以触及。
而花焰瑾的此处妙穴又有不同,曾有医书唤做潜欲销魂窝,万中无一,能入此窝者必被宫压穴揉,难以坚持一分半刻,便要一泻千里。而着最为娇弱的秘处,也是女人最为酥痒的软肉,纵然你是坚贞烈女,这深窝蜜肉被肉棒一碾,也得大泄不止。
这红缨枪挨着岩浆似的蜜汁一烫,沿着肉杆四散而下,炙热的温度连花焰瑾自己的穴中蚌肉也烫的麻酥酥,顿时飘飘欲仙。
宋流风在那销魂窝里坚持了半晌,终于把持不住这四面八方的细咬,抽离窝穴,那软嫩的宫口适时落下,将那秘处藏掩,却又正对着蓄势待发的枪尖,宋流风腰眼一麻,枪尖抵上那柔软若无骨的小口,玉卵提升,一股股也胜似岩浆的浓白稠汁,对着小口狂泄不止。
“呀啊!哈~好烫!嗯……”花焰瑾猛地打直背脊,灵台间感受到一股股滚烫的汁液悉数打进秘宫,炙热的温度和宫内的蜜汁混杂在一起,不属于自己的体液更加感觉分明,通过花房,浅浅温暖着深藏的销魂窝。
舒爽的呼声从二人口中传出,粘稠的液体从二人交合处绵延落下,而四周气流微动,只见二人高潮之际,不忘提神运气,细细的将对方泄掉的精元默契的纳入体内,雌雄相吸的特殊精气,让爽方沉溺三分。
“这下是本侯赢了吗?”
“哼……依奴家看,是双赢吧。”
……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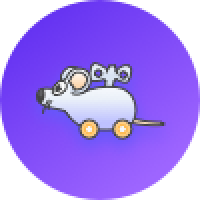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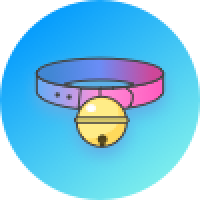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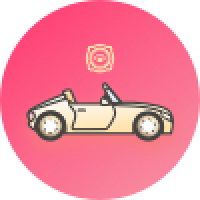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